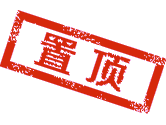抢注商品通用词、热搜词甚至网红的名字,然后发起商标侵权投诉,意图并不在投诉本身,而是通过投诉索要高额授权费、撤诉费,甚至以“通知-删除”规则相要胁,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这一商标领域乱象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1月22日,清华大学法学院组织邀请十余名专家、学者及字节跳动、快手、阿里巴巴巴巴等平台代表,研讨商标抢注和恶意投诉现象的治理与规制。
与会嘉宾指出,商标的抢注、囤积以及随之而来的以恶意投诉进行牟利问题已成社会公害,是一股扰乱商业秩序、破坏营商环境的“商业水军”。专家认为,此类“打着法治来破坏法治”的恶意行为愈演愈烈,应予刑事打击。
商标抢注、囤积牟利是破坏营商环境的“商业水军”
河北秦皇岛某公司抢注“自卫”商标后,批量投诉上百家情趣用品网店,扬言“要撤诉,给五千”,而投诉者还申请注册100多个诸如“DIESEL”等国外大牌及电商卖家通用的商品描述词汇。2020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自卫”商标系恶意抢注,宣告无效。

更有甚者,有公司抢注商家通用的描述女装风格的“超仙”(超级仙女)作为商标后,批量投诉了电商平台销售的8000多个商品;抢注“水桶”商标,却用来投诉商家售卖的水桶包。还有人抢注“破洞”、“呼啦圈”等,投诉无数破洞牛仔裤、呼啦圈的电商卖家,试图勒索高额授权费、撤诉费。
不仅电商平台,快手、B站等社交和视频平台也备受其害。
快手高级商标顾问招阳介绍了一个案例:山东某公司抢注快手拥有1000余万粉丝用户的“刘妈妈”作为商标后,索要200万元赔偿。快手帮助“刘妈妈”搜集大量在先使用证据,并支持“刘妈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请求。2020年9月,国知局裁定山东公司无正当理由囤积商标,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其抢注的“刘妈妈”商标宣告无效。
“由于网络平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抢注者往往不只针对单一的商家或者产品,而是批量抢注、批量投诉,并借此谋取高额利益。”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商标的抢注、囤积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意投诉并非全新的社会现象,但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已呈现出新的样态,即通过抢注各平台上被用于描述商品的关键字、网络热词、网红店铺名及网红的名字(姓名、花名、艺名),然后向平台进行商标侵权投诉,其意图并不在投诉本身,而是通过投诉索要高额授权费、撤诉费,甚至以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相要胁,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与会嘉宾认为,在上述情形中,我国商标法对于商标的保护制度被一些恶意主体异化为牟利的工具,扰乱正常商业秩序,危害行业发展,浪费行政、司法和社会资源,与刷单、刷评、恶意索赔等网络黑灰产群体类似,是破坏营商环境的一股“商业水军”。
“在‘刘妈妈‘案件后,我们对平台很多用户进行了普法宣传。平台和用户都应积极维权,收到恶意投诉和起诉积极应对,不纵容、不惧怕、不妥协。”招阳表示。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德璋表示,对于此类严重影响网络营商环境的“商业水军”行为,阿里已经建立起一套规则进行监控和识别,同时配合执法司法机关、联合权利人及商家进行打击,一方面积极引导商家进行在先销售证明或者商标构成通用名称等证据材料取证,同时通过正向引导、技术赋能,提供品牌保护等知产服务。
“以法治的名义破坏法治”,亟需刑事打击
“要彻底解决类似的问题需要花费很多资源,成本非常高,这已经成为社会公害。”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国斌认为,除了从源头上通过规制恶意抢注来规制恶意投诉,在商标法意义上强化使用目的,也可在刑法上设立规制措施。
“抢注网络用户、平台商家普遍使用的商品描述通用词,然后投诉平台数千商品侵权,此种情形可能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网络法研究所讲师郭旨龙认为,被用于描述商品关键字、网络热词、网红店铺名及网红的名字,就是网络平台经济中经营活动的重要要素,网络平台具有一定的管理和裁判职能,当这种职能被欺骗、滥用,导致网络平台上的某一经营活动没法顺利进行时,应当认为网络平台经济中的特定经营要素已经被破坏。此外,行为人以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相要挟,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网络平台商标抢注与恶意投诉的刑法治理,一是需要网络刑法条款的关键词解释跟上网络平台经济时代的背景和需求,二是需要与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前置法进行有效衔接,最终发挥好刑法的宣示表达功能和强制威慑功能。”郭旨龙表示。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指出,商标流氓问题的出现,是一种“以法治的名义破坏法治”的法律异化现象,当私法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时需要公法的参与,“应当通过司法裁判指导性、有影响力的案例使得通过法治来谋利、借助法治反对法治的法律异化现象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