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醋
2011年初微信上线,那时候的人们大概想象不到,手机里曾经最重要的通讯录和短信功能会在十年内显得无足轻重。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它会从“下一个QQ ”的标签里挣脱出来,甚至腾云驾雾,整个颠覆了中国人的通信和社交方式。
而以微信公众号为始,微信从简单的通信工具逐渐走向一个商业生态。微信变成一个巨大的流量池,同时又是一个生意场。许多人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看到了它带来的互联网创业机会,于是抖擞精神,融入进来。这款国民产品的十年历程,他们是其中更深刻的体验者。
“我把微信群禁言了”
最初的微信版本与手机短信一样,只有收发文字和图片的功能,2012年4月朋友圈的上线是分水岭。随着2010年以后电商平台与快递业的发展,线下生意为主的传统形式正在被打破,而在这个只好友可见的分享空间里,一些人也看到商机。
现在回到了宁波的白雨2013年开始做“微商”的时候,这个词还不流行。
白雨喜欢布料,存着很多质地很好的布料,大一暑假自己做了口金包背到学校受到追捧,因此决定批量做试试。她来做包,另一个朋友负责包装的设计——每个包都会用手绘的牛皮纸袋包着。“我在杭州上大学,所以会把包拿到杭州甚至上海的复古集市上去卖,同时我也会在朋友圈里发发包的照片。”
口金包卖了一年多,卖了150多个,虽然不多,但也赚到了些钱。从卖口金包开始,白雨学着用微信和朋友圈来做生意。这在读大学的女生中变得越来越常见。
据统计,2014年微商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而到2020年,几乎每14个人中就有一个微商。超过六成微商的年龄区间在18-25岁,而其中超过80%的微商是女性。
从口金包到之后的日本代购和海淘,到后来又做了医美,白雨逐渐有种离不开微信的压迫感。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身边的朋友某一天开始突然转做微商,朋友圈开始不节制地野蛮生长,最后不得不屏蔽他/她,或者索性关掉朋友圈。但事实上,对于对立面上的微商们来说,有时候也是无奈选择。


白雨大学时做的口金包
“我会自我怀疑,我为什么要发这种东西,特别是生意不好的时候。但是还是要发,不能让大家忘掉我。”白雨说。
白雨身边的人一直觉得她是那种离铜臭味很远,偏艺术的女生。但在做微商后,她也要每天发8、9条朋友圈,配上文案和九宫格图,满满当当。
“一开始就是硬着头皮发,但又为了不太过有“铜臭味”,我会很精心想文案。很多人都说我是他们唯一不会屏蔽的微商,但因为这样,我要很绞尽脑汁地想那些文案,非常累。”
但哪怕这样,她仍然在频繁的自我否定。时常做一阵子就因为微商的形象太不入眼而放弃,但一段时间后又因为回报实在很高而重新回来。
“我刚用微信是大一,在朋友圈发些伤春悲秋的东西,那时候那里是个理想国。后来做了代购开始,朋友圈就只是一个工具了。”
在很长时间里,白雨都只说自己是做代购的而不是微商。“卖三无产品、减肥药这些的才是微商”,虽然微商在2020年被纳入正规职业,但这种“假货暴利”的负面印象仍然延续。
白雨不太爱讲话,但也不得不像通常的微商那样,不停地加人,拉群,不停歇地回复消息。
“你不能让他们等超过3分钟,大家的购买欲就在一瞬间,这时候你接上了这股劲,东西就卖出去了,没有及时回,可能对方就不想买了。”
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要攥着手机,在宿舍公共浴室洗头的时候,手机响了也要擦一擦手回消息,甚至去看电影、考试也要提前发朋友圈告诉别人自己要“消失”几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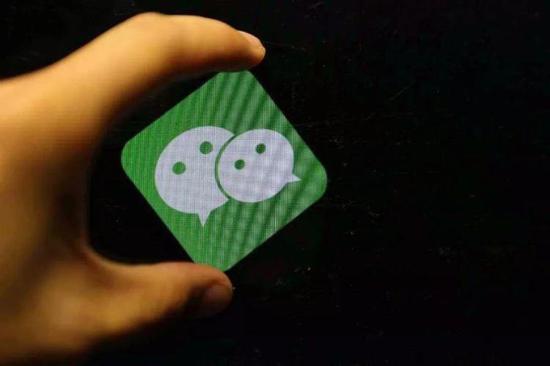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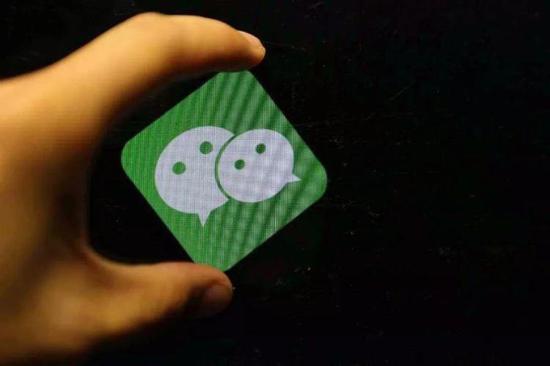
白雨用赚来的钱在毕业时候去台湾玩了半个月,也没有忘记一并提回来800多片面膜。
“要做微商,就没有隐私可言。”
她的通讯录里躺着3000个微信好友,拉了一个500人的微商群。但她把群禁言了,在群里除了她发上新的信息,没有别人可以说话,至少这是可以再争取回来的一丝空间。
“10w+”的焦虑
在朋友圈以外,另一件变革性的事件也在2012年发生——公众号出现了。
从QQ沿袭下来的微信在一开始就足够瞩目,每个新功能的出现都不乏跃跃欲试的拓荒者。但那时候还叫微信公众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引来不少质疑。
知乎上至今仍然保留了一些2012年末前后用户们对公众号的评价。
“微信本质上只是一个通信工具,至于新媒体神马的,都是忽悠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作为媒体,MP(媒体平台)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强烈的需求。”
后来的故事所有人都知道,微信公众号成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字内容创作者最重要的阵地。在互联网上已具雏形的新媒体纷纷在公众号上开了号,除此之外又酝酿出大量以个人或小团体驱动的自媒体。面对着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的千万个公众号,站在对面的传统媒体仿佛一夜之间被革了命。


相比于依靠朋友圈和社群创业的微商,微信公众号的商业化潜力被更好地挖掘了。2013年微信公众平台细分为订阅号和服务号,隔年新增阅读次数和底部点赞按钮,也是在2014年,公众号新增推广功能,广告进入公众号。
在公众号写文章变成了一个实打实能赚钱的活儿,但这块蛋糕里能分到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有多热门,能被多少人看到。
一时间人人都在追逐流量,希望文章末尾能出现那个如勋章一般的“10w+”。
随着唯流量论而出现的,是“标题党”、“蹭热点”和诸如“兴奋学说”的逐渐流行。
兴奋学说: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是——出现刺激情景,产生评估,反馈情绪。我们身边总有些群体,当一个人或某件事或一个观点,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这类群体就会变得很兴奋。他们一兴奋就会为你制造更多的热度。
2018年这种唯流量论的公众号流水线爆款潮达到顶峰。一家名叫瀚叶股份的上市公司用38亿收购了量子云,后者是一家依托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新媒体公司,旗下运营着981个公众号,主要涉及情感、生活、时尚等领域。而应付着合计近2.4亿粉丝的,加起来只有50位编辑。
在流量至上的氛围里,流量焦虑包裹着所有在公众号阵地上生产内容的创作者,33岁的北漂张克就是其中之一。
张克从2017年开始写教育类的公众号。他也会模仿一些爆款文章的写法,比如粥左罗或者刘润,比如三段论和红色大标题,但是变化不大。
“同样的内容粥左罗就能是10w+,我就只有几百上千的阅读量。我甚至写过一篇类似《我写了4年终于凑够了10w+》的文章。”
像张克这样没什么影响力的内容作者是公众号生态里的大多数。在用户的阅读习惯已经培养起来后,新的内容原创者来越难被关注到。
QuestMobile取了2019年2月的数据来做分析,结果显示虽然80%的微信用户在看公众号,但其中73%的人关注的公众号少于20个。
公众号去年将推送时间轴打乱并且上线点赞分享按钮,从私域流量试图转向智能推荐,都是为了将这摊已经分出层次的死水重新搅浑。但对于大部分公众号原创者来说,仍然是大树底下,寸草不生。
拐点发生在2017年前后。有数据显示,2017年微信公众号数量已经超过2000万个,但是平均打开率(打开率=打开文章人数/粉丝数)只有2%左右。也就是说50个订阅者中只有1个人会点开文章阅读。公众号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但却变成了少数人的狂欢,单打独斗的新晋者往往无法养活自己。
“保护用户”?
但是做播客的杨一反而在这个曲线的下坡路上捡起了公众号这块阵地。杨一现在是播客公司JustPod的联合创始人,但在2018年公司名字都还未注册的时候,他就开了一个叫「播客一下」的公众号。在跳出来创业播客前,杨一是一位媒体人,眼下的公众号在他看来已经很难成为内容创业的土壤,而变得更工具化。
“之前可能有人靠公众号创业,比如说我的同事可能在2013开了个号,2014年就辞职离开了媒体,专心做公众号,后来就变成比如行业里的一个KOL,也能养活自己,甚至一个团队。但现在可能不太行了。”
对杨一来说,公众号现在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播客的渠道,作为一种工具存在。
“现在的公众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层里看自己关心的东西,”杨一说,“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关注点,我愿意看营销号,你愿意看咪蒙,然后别的人可能愿意看专业媒体写的非虚构稿子。我们各取所需,但是互不干涉。”


“传统媒体的坏处是,媒体强迫所有的人和我欣赏一样的同样的东西;社交媒体的坏处在于,所有人的趣味混在一起,发生不必要的争论。”在这一点上,杨一甚至觉得公众号自己也在有意的“工具化”,比如它仍然保持着平台本身的强主导型,而避免成为微博一样的舆论广场。同时细节上的一些改动,让用户更接近自己关心的内容。
“很多平台都最多只能做成媒体,但因为背后巨大的用户量,公众号可以做成工具——不是所有的平台都配成为‘工具’。”
杨一在2020年用公众号非常系统地去做一些播客的普及,讲一些国外的节目案例,以及国外各种播客品类的玩法和合作方式。音频作为内容媒介在国内还很年轻,生态未形成。按他自己的话说,“还需要一些外力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行业一点”,这是用公众号可以做的事。
互联网越来越变成一个流量生意,微信生态里的创业者们不免落在追逐流量的圈套里。但在刘兰看来,微信本身一直持着保护用户的立场,“特别是在外面几乎所有产品都在套路用户的情况下”。
2018年年底微信撤下了上线4年的公众号底部点赞功能(2020年7月重新上线),2019年初刘兰进入微信团队,做了一名产品经理。
保护用户的理念一直为张小龙所强调。但另一方面,刘兰觉得这种“保护用户”的姿态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微信赚钱的方式没有那么过分,因为毕竟它不像别的产品那样往往面临激烈的商业竞争。”


南方通信大厦10楼时期的微信团队
“我原来很崇拜张小龙,现在只是觉得他比较厉害”,刘兰说。
在微信从产品成长为平台,变成10亿人的生活基建后,焦虑感也在微信内部加深。
微信自己也在焦虑
“微信作为一个平台已经很成熟了。比如小程序这一块,更多的增长依赖于生态里的开发者们,但这一切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近两年进到微信小程序团队的新人,做与平台迭代相关的工作会比较多,但到去年下半年开始,小程序的架构已经趋于完善,可做的事情不多,这导致一些近两年新进来的员工显得无事可做,转而离开微信。
“很多同事离职了,但同时老板又要招更多人来做事,哪里都在内卷。”一位接近微信小程序团队的人士表示,两年前微信小程序团队只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扩充了一倍。
在2021年微信公开课上,微信小程序2020年的数据喜人。突破4亿的DAU(日活)用户,67%的人均小程序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以及68%的小程序数量(有交易的)同比增长。
一家做互联网线上保险业务的公司在App和小程序中选择了后者。“相比于小程序,App有时候显得太重了,虽然他有更丰富的功能,但是并不方便大家去点开和传播。”
同时,对开发者来说,小程序相较客户端需要安卓与iOS并行的情况,开发成本至少要节省一半。
但在小程序团队内部基本不看DAU,而交易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团队在2020年第一次有了数字上的压力。
“之前微信小程序团队没有这方面的硬性压力,去年开始有了指标要求。指标主要以交易为主,关于交易笔数或者小程序数量的增长。”前述接近微信小程序团队的人士表示。
微信小程序从2017年初上线之后,对大量企业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在疫情冲击下,线下转线上的趋势在2020年进一步加速。过去一年食品、日化等行业企业的小程序GMV同比增长超过500%。
但另一方面,出于保护用户的考虑,小程序并不能像App一样主动触达用户,这显然会对内部团队KPI的完成带来困扰。


微信团队近半数人现在所在的T.I.T园区
在微信团队最集中的广州TIT园区里,拼多多小程序的团队在微信隔壁租了半层楼。许多因为微信这块产品的金字招牌而进入微信,后又因为成就感不足或者薪资原因而离开的人,下一步的去向都是其他互联网大厂,近两年最热门的下家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靠私域流量起来,所以微信内部可以看到拼多多这几年的数据和发展状况。从2016年开始就有很多人从微信去拼多多了”,刘兰透露,“包括现在拼多多小程序的负责人,原来就是微信的。”
但刘兰也坦言,这种功能趋于完善而发生的停滞,是进化出平台属性的产品都会面临的瓶颈。
视频号来了
而不管是公众号还是小程序,从去年开始都暂时退到了聚光灯后面。
2021年的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上台讲了一个半小时,其中一个小时都放在了视频号身上。视频是他所认定的未来主流的媒介语言,也会是微信急需的下一个想象空间。
张小龙表示,对视频号的预期是其背后所带来的第二套身份体系。如果把“视频”和“号”拆分开来理解,“号”的意义更大,而前者则是一种顺应潮流的选择。
“如果能理解原来公众号的定位,也就能理解现在视频号的意义。”而视频号的门槛比公众号更低,更容易变成在微信上人人都能具备的第二重身份,也因此是微信生态里最适合担当连接器角色的一个。


现在的状况是,2亿人的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公众号的马太效应明显,微信迫切地需要视频号这源活水。
“小龙去年三句话不离视频号,而且这一年视频号的迭代这么激进,我们也很惊讶,有种一路绿灯的感觉。”一位微信员工表示。
张小龙透露,产品研发初期对视频号的定位是“视频化的微博”。在朋友圈、公众号的内容生态逐渐压抑或闭塞的时候,微信需要这样一个私密空间以外的“广场”带来转机。
杨一觉得这样的转变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但这也给另一些人带来新的机会。
张克从去年9月开始就转向了视频号,现在已经是一个1w粉丝的金V博主,相比之下,经营了3、4年的公众号上还是只有3000多粉丝。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保持日更,有时候一天会更3、4条。对我来说视频号更自然一点,我可能属于视频输出型,很多脚本都是临时想的,不怯场,也没有太多顾虑。”
他最近刚买了绿幕和专业灯光设备,也表示未来会往更专业的视频方面尝试。
“现在的视频号还不完善,但反过来想,这样和平台慢慢长大也是很好的。如果视频号现在的商业形态很完善的话,(我)能不能接得住也是个问题”,张克说。
随着微信生态逐渐走向公域,与外界的联结加深,这里会是更多人互联网创业的发迹之地。与此同时,关于流量的焦虑也仍旧绕不开。
但也有人并不追赶浪潮,选择在流量的焦虑中抽身。
白雨在去年六月告别了微商身份,从杭州回到了宁波。她解散了微商群,也把朋友圈的广告锁了起来。
“我现在去外婆家都不想带手机,因为还会有条件反射。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取完票就强迫自己关机,一直到看完电影回到家再打开。”这位7年的微商,现在想远离这种与微信捆绑的焦虑感。
“有时候我更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白雨说。像白雨或是杨一一样,微信终于还是在一部分人的手里回归到了“用完即走”的状态——如张小龙所说——退身成为一个“优秀的工具”。
这是微信第一个十年的故事。有人活得很好,也有人选择退出了这场潮水。下个十年,还会有更多的人尝试在“公域”和“私域”之间找到平衡,靠它的生态赚钱,也继续感受着它带来的焦虑,并学着与之共存。

